
農曆正月廿一是淨土宗第九代祖師蕅益大師圓寂日。蕅益大師生活在明末清初,這是一個國土板蕩、風雨飄搖的時代。但即使處在這樣的環境,佛教界也出現了如蓮池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這樣的中興領袖,其中,蕅益大師一生為法忘軀、精勤不已,且貫通儒釋、著作宏富,終成為名滿天下的淨土宗祖師。
然而,少年時的大師卻是反對佛教的,那麼,他是如何盡棄前非,最後又歸心淨土的呢?這是一個極其傳奇又曲折的故事。
以千古道脈為己任
據《年譜》(弘一大師撰)記載,蕅益大師生於明萬曆二十七年(公元1599),俗姓鐘,名際明,又名聲,字素華,又字振之。晚號「蕅益老人」,別號「八不道人」。江蘇吳縣木瀆鎮鐘氏子。父名岐仲,持誦大悲咒十年,母親金氏夢到觀世音菩薩抱著一個小男孩送給她,生下了後來名聞遐邇的大師。
當時的父母已經四十歲了,年齡老大,加上好不容易得來的一個孩子,自然寵愛有加。因生在佛化家庭,大師很早就開始誦經禮佛,七歲吃素,而且持齋非常嚴格,曾經夢到觀世音菩薩相召勸勉。
到了十二歲,父母送他出外就學。這時候的大師讀了很多儒書,虔心於格物致知之要、居敬慎獨之功,張揚得意,以傳承儒家道統為己任。不僅作了數十篇雄赳赳、氣昂昂的論文批駁佛教,而且從小茹素、久斷葷腥的他這時開始喝酒吃肉了。此舉真令父母大跌眼鏡!要是換做今天,恐怕父母早就氣急敗壞地四處追著打了。
傾心佛教,淹貫諸宗
然而,蕅益大師的父母畢竟是講道理的。母親嚴厲的教誨,又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閱讀了蓮池大師的《自知錄序》和《竹窗隨筆》,才幡然悔悟,從此不再謗佛,並將以前所有闢佛的文稿付之一炬。
二十歲時,詮釋《論語》「顏淵問仁章」中孔子回答顏淵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對「天下歸仁」之語起發疑情,隨即苦參力究,不能下筆,廢寢忘食三晝夜,大悟孔顏心學。
然而此時,父親不幸亡故,大師為父親誦《地藏經》超拔,由此萌生出家之心。
後聽一法師講《楞嚴經》中 「世界在空。空生大覺」 時,懷疑為何有此大覺,能為空界做出預先安排,悶絕不知所措。此時決意出家,體究生死大事。
天啟二年,在一月中三次夢見憨山大師,痛哭緣分淺薄、相見太晚。本欲從憨師出家,然而千里迢遙,遂依憨山大師的高足雪嶺禪師出家,命名智旭。
出家後的大師如魚得水,飽餐佛法甘露,於宗門教下,深參力究。第二年夏,坐禪於餘杭徑山,體究功極,身心世界忽皆消殞。因知此身從無始來,當處出生,隨處滅盡,但是堅固妄想所現之影,念念剎那不住,的確非父母所生。自此,性相二宗,一齊透徹;一切經論,禪宗公案,無不現前。隨即覺悟到此境界非為聖證,故絕不語一人。久之,則胸次空空如也。這個境界,即是天台「六即」中的「名字位」。
二十八歲那年,母親病重,大師回家親自侍奉湯藥,並四次割身肉做藥引,冀望以此孝心令母親增福延壽。然而,母親最終仍然病亡。料理完喪事後,即往深山閉關,以參禪功夫求生淨土。
大師看到當時戒律衰頹,為匡正戒律,閱律三遍。雖然對於戒律的解悟很深,但自愧煩惱習氣強烈,行持不夠,故終其一生從未與人授戒。
三十二歲時,大師私淑天台,究心台部。以天台教觀匡救禪宗之弊,尤志求五比丘如法住世,令正法重興。
矢志安養,一意西馳
永曆二年,大師已經五十歲了。某天他對成時法師說:「我從前念念想要恢複比丘戒法,近年來卻念念想著求生西方了。」成時法師聽了非常驚訝。後來才知道,大師在家時發大菩提願,後來為匡救聖教,終生孜孜力行。
徑山大悟後,徹見近世禪者之病,在絕無正知見,非在多知見,在不尊重波羅提木叉,非在著戒相。故抹倒禪之一字,力以戒教匡救。尤志求五比丘如法共住,令正法重興。後決不可得。遂一意西馳,冀乘本願輪,仗諸佛力,再來與拔。至於隨時著述,竭力講演,皆聊與有緣下圓頓種,非法界眾生一時成佛,直下相應,太平無事之初志矣。
由此思路一轉,大師晚年就專修淨業了。在《自像讚》中,大師自況:「不參禪,不學教,一句彌陀真心要。不談玄,不說妙,數珠一串真風調。」 念佛矢志淨土的目標確定,又假之以懺悔自訟,洗濯心垢,藉此慚愧種子,方堪送想樂邦。大師以身說法,感人至深。
大師的文字般若皆從徹底悲心中流出,可謂婆心切切。故日本京都沙門光廉比丘在1723年重刊《靈峰宗論》序中說:「餘亦嘗言,讀蕅益《宗論》而不墮血淚者,其人必無菩提心。」蓮宗十三祖印光大師敬仰讚歎蕅祖「言言見諦,語語超宗,如走盤珠,利益無盡」。又讚言「宗乘教義兩融通,所悟與佛無異同。惑業未斷猶坯器,經雨則化棄前功。由此力修念佛行,決欲現生出樊籠。苦口切勸學道者,生西方可繼大雄。」
印光大師又曰:「若論逗機最妙之書,當以《淨土十要》為冠。而《彌陀要解》一書。為蕅益最精最妙之注。自佛說此經以來之注,當推第一。即令古佛再出於世,現廣長舌相,重注此經,當亦不能超出其上。」此言可謂高山仰止,心心相應之語。
永曆八年,大師示疾,當時他寄給錢牧齋的信說:「今夏兩番大病垂死。季秋閱藏方竟。仲冬一病更甚。七晝夜不能坐臥。不能飲食。不可療治。無術分解。唯痛哭稱佛菩薩名字。求生淨土而已。具縛凡夫損己利人。人未必利。己之受害如此。平日實唯在心性上用力。尚不得力。況僅從文字上用力者哉。出生死。成菩提。殊非易事。非丈室誰知此實語也。」
大師病到七日七夜不能合眼,唯有痛哭稱念佛名,專求佛力救拔,這對自負高慢者,不啻當頭一棒。
清順治十二年(公元1655)正月二十一日午時,大師趺坐繩床,向西舉手而寂,世壽五十有七歲,法臘三十四。僧夏從癸亥臘月至癸酉自恣日,又從乙酉春至乙未正月,共計夏十有九。
流水有心終匯海。縱觀祖師一生含辛茹苦,護持聖教,為報四重恩,樹立禪、教、律、密、淨之正法,匡正儒家宋明理學之弊端,救世之慈心、宏願、深忍、大行。最後導歸淨土,藉乘本願輪,再來救度娑婆苦難眾生。其深慈大悲,貫徹始終,令見聞者無不興起,被後世奉為淨土宗第九代祖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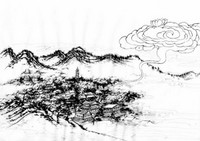











 玄奘大師
玄奘大師 大安法師
大安法師 如瑞法師
如瑞法師 慧律法師
慧律法師 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 省庵大師
省庵大師 界詮法師
界詮法師 善導大師
善導大師 妙蓮老和尚
妙蓮老和尚 聖嚴法師
聖嚴法師 蓮池大師
蓮池大師 其他法師
其他法師 憨山大師
憨山大師 廣欽老和尚
廣欽老和尚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虛雲老和尚
虛雲老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