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五九年出生的,六零年鬧饑荒,六零、六一、六二連續三年都鬧饑荒,以後也都吃不飽,有得吃但是吃不飽。一直到八五年我去北京讀書的時候還是吃不飽。為什麼吃不飽呢?糧食是限量供應的。現在小孩子會奇怪,說這麼多糧食為什麼要限量供應?有一次我跟我外甥外甥女講我們當時吃不飽,他就說你幹嘛不吃飯呢?我說糧食是限定供應,他說為什麼要限定供應啊?我說缺糧,他說糧食多得很怎麼缺糧啊呢?缺糧,那個年代就這樣。
我去北京的時候還是二十幾歲的小夥子,很能吃。我們一個月限量三十五斤糧,一天一斤多糧,不夠吃,吃不飽。過去這麼大的碗,我能吃兩碗米飯,可是不夠量,沒辦法只有一碗。每天都吃不飽,天天早早就盼著什麼時間開飯呢?餓!真的是這樣。那個年代就是吃不飽,大家都在挨餓。
在家裡我是多餘的人,我爸總是覺得我給他帶來很大的負擔。家裡窮嘛,多了個男孩就要建房子娶媳婦啊等等。他壓力大,幾次要拿我去送人,我爺爺不肯,沒送出去。有一次送出去,我大哥又把我背回來了。我非常害怕。我兩個哥哥小學畢業,我爸說哥哥小學畢業,能夠記個數、看個票據就可以了,你就別讀了。就這樣,我九歲放羊,十一歲放牛,十三歲才開始讀書。十三歲去讀一年級,老師說歲數大了,從一年級開始讀,啥時候才能畢業啊,要麼插班吧,就讓我直接從三年級開始讀。
我們那時候小學讀五年,初中兩年,高中兩年。那年代天天念毛主席語錄,說毛主席教導我們,教育要革命,學制要縮短,不要學太長。你們歲數大一點的可能知道。
在家讀書對我來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讀不明白啊,連爬帶滾。你看現在發信息我都用筆畫,小學沒學過拼音,拼不來。拼音是一二年級學的嘛,到了三年級就不教拼音了,完了就弄不來,怎麼都拼不准,到現在也是這樣。南方人講普通話也不標準,比如 「花」、「發」 這兩個字,南方人讀法是一樣的,都讀「花」,念不清楚,輕鼻音、重鼻音都搞不清楚的。讀書的時候每次考試我就是六十分萬歲 ,能考六十分就不錯了,因為沒有基礎,學習一直很困難。
我讀書的時侯正好碰上文革,國家提倡農業學大寨。學校也種地,學生基本上不上課,每天就去地裡幹活。我們學校有好幾畝地,就搞秧苗研究。老師帶著我們看這個秧苗怎樣生蟲,生在哪裡。我們那時候小,大家就在田裡玩,抓青蛙、抓泥鰍,後來又到山上去開荒種茶。小學還有考試,初中就不考試了,考卷可以帶回去做,過一個禮拜交上來,那就胡亂抄唄。就這樣這叫什麼讀書嘛?
好不容易混到文革結束,我也畢業了,就這樣子。你看很慘吧,所以基本上沒讀什麼書啊。我那時候所謂的高中畢業相當於現在小學三年級還不到,還沒有他們認的字多,學得多。不怕你們笑話,蓮池海會那個會字,它那個繁體字,我都不認識。那個時候破四舊不讓學繁體字嘛。我第一次到太姥山,南無那個「無」 字,它的繁體字寫法,我說那個念什麼呢,不認識。
以前學的文化非常有限,所以出了家以後有機會學習,我都非常非常珍惜。這就是人生經歷不同,遭遇不同,態度就不同。後來到佛學院讀書,我真的沒浪費一點時間,一有時間我就在學習。同學們文化程度比我好,他們可以玩,我都不敢玩,拚命學。他們租小說看,我說那個東西對我沒用,我就不看。學校有圖書館,館裡有幾十萬冊的圖書,一有時間我就去圖書館借書看,很多經典都是當時在佛學院看的。
我十三歲讀書的時候,我媽帶我去寺院。那個寺院叫靈峰寺,靈峰寺挺大的。我到了那裡,感覺哎好像這個地方曾經來過,就很喜歡那裡。因為文革,寺裡的人都穿俗服,穿普通老百姓那個衣服,但頭還是剃光的。白天干活,晚上回來他們就偷著做功課,外面派人放哨。如果有工作組過來,趕緊停了;沒有來他們就繼續念經。南方好一點,山高皇帝遠嘛,他們還能堅持一直素食,早晚課誦。那時我就很喜歡聽到念經的那種聲音。當時住了一宿,回去後我就還想去,我說我很喜歡那些和尚,那個寺廟真好。我媽說好啊,你喜歡就好。
過了一年她又帶我去太姥山國興寺,我們村裡有一個老人家在那裡出家。那年我十四歲,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在家裡過過年。過年放假,幫著家裡幹完農活,大約臘月二十七、二十八,我就到廟裡去。廟裡老人家會誇小孩子,說這個小孩真乖呀,真能幹呀,挑水、搬柴、掃地、端菜都能;一誇,小孩子就越願意去啊。老和尚也好,老居士也好,都誇我。我一般正月初三初四回家,在廟裡住一個禮拜左右。本來在廟裡吃飯要交錢的,自己帶米,要給廟裡交兩塊錢的伙食費,後來他們說這個小孩子幫廟裡面幹了不少活,不用交伙食費,這樣我就可以攢下兩塊錢。從此以後,我幾乎都在國興寺過年。
暑假不能去廟裡,暑假要雙搶。南方水稻都種兩季,雙搶就是搶收、搶種。第一季的水稻熟了趕緊收回來,第二季的水稻馬上種下去。暑假要在生產隊幹農活賺工分,沒時間去了。到了冬天,過年時候就就可以去廟裡。聽那些老和尚講一些道理,其實他們也不懂太多佛法,也就是用一些簡單的勸世文之類的講講, 我就很喜歡聽。我說這個很好,哪一天我也要出家。
初中畢業我就想去出家,我爸不肯。不肯那就混到高中,到高中也不肯。我爸死活不肯,不過我媽堅決支持。我就準備在國興寺出家。遇到一個歲數比我大三四歲的人勸我不要在這裡出家,說這裡都是老人家,他們啥都不會。他勸我去平興寺。他就給我介紹了個師父,就是我的剃度師。我師父十八歲就出家了,沒讀過書沒什麼文化。他也挺苦的,孤兒,父母雙亡,出家以後跟我師爺呆了十七年。我師爺會打人,經常揍他。去居士家裡,我師爺不讓他進門,就讓他站在門口,居士叫他進來他也不能進來。到了可以受戒的時候,我師爺不開口,他不敢去受戒。一直等到五幾年,好像是最後一堂戒他才去。那時候掛的是虛老作得戒和尚,實際授戒是本煥老和尚。
他們說我師父有過參學,叫我到這裡出家。我就來這裡看看,遇到這裡的一位出家師,他說這裡是農場,幹活累個半死,你哪裡受得了,你千萬別來,再說你高中生也不可能出家。那時候高中畢業很好找工作,我高中八十幾個同學中就只有一個當農民,其他都很不錯的。那個年代高中生出家好像挺轟動的,不像現在,現在博士生出家都很正常,時代不一樣了。我在這裡看了看,覺得這個地方還可以,天天干活,幹就幹唄,來就來唄,我就這麼來這裡的。
我從十三歲開始接觸到佛法,只是喜歡這種生活,喜歡聽和尚念經。沒有任何理由就喜歡念經那種聲音,聽到他們唱讚都會流眼淚。他們唱讚沒有麥克風,也沒有現在唱得這麼好聽,全都是老和尚,但是我就是很喜歡聽,就是這樣。然後我說將來我要去當和尚,高中畢業我就來了。我爸一直不同意我出家,我硬要出家,那怎麼辦呢?他就說你要是出家了就不能再回來,如果回來,我第一個把你媽給埋了,再把你給埋了。他說我媽把我忽悠出家的,出家再還俗,回去很沒有面子。我說一定不會回來!
我一直本著這個宗旨,我出家不能還俗,不能有退回的因緣。不能回來,沒有路了,無路可走,怎麼辦?那就必須走好!我不想當一個賴賴唧唧,被人擢著脊樑骨的和尚。自己起碼要有這麼一個志願,當和尚,不能當得破破爛爛、就混個飯吃,這過得啥意思嘛,起碼要有志氣,要學習,要修行。
我今天這樣,不是我自己設計的,都是因緣,很多的因緣。佛法講因緣是不可思議的,你要說我現在出名,也是因緣出名的,不是我有多大的本事。我跟大家攤了牌,我沒多大本事,啥也不會,按現在標準我幾乎是半文盲啦,外文我也說不來。我們那時候不學外文,那個時代說是美帝國主義的東西,反美反帝不能學ABC,不學ABC照樣幹革命。那個時代就是這樣。現在我歲數大了也學不了。我上佛學院有開這個課程。當時我想,學這沒有用,我不可能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學習另外一種語言上,漢語我都學不明白,現在還再學一種外語。學外文都是從單詞開始吧,這是桌子,這是板凳,這是圓珠筆,這是鋼筆,這是蘋果……一個一個念,然後串起來,那什麼時候學得會啊。一個字一個字拼起來的,你才會讀文字的嘛,學外文也是這麼學,很困難。所以我真的沒本事。
都是因緣,我佔了幾次第一。這個地區高中生出家就我一個,是佔優勢了不是;八零年中國佛學院剛剛恢復招生我是第一批去讀的;文革以後恢復受戒,我也是第一批;九零年我被新加坡請去講經,文革以後大陸到國外弘法這也是第一次,我就是這麼出的名。現在就沒有這種情況了,現在都要靠自己的實力。
所以說我是莫名其妙出名的,我不是講經講得多好啊,也不是別的方面有什麼特長,都是某種因緣讓我出了一點小名氣而已。我還沒有來這裡學戒的幾位法師學得好,我是自己學的,沒人帶。後來他們逼著我上台給他們講課,我說我平時也就是自己翻翻書而已,叫我講課很困難呢。他們一直逼我,開始有三四個人,我說三四個人怎麼講,十幾個人還差不多。後來七整八整,真的整出十個人來,他們說已經有十幾個了,你講不講?那就講吧。講兩天我生病了講不了;後來又走了幾個人,我說沒人了就不講了;過幾天又來了人又得講。就這樣是被逼出來的,要給別人講課你自己就要拚命去看啊。
那時候很忙,又要搞基建,又要講課,都要花時間,搞得很匆忙,所以脾氣非常暴躁。我沒備完課,誰要是吵我,我肯定罵人的:「幹什麼?吵吵吵?吵什麼吵?」就這樣,這麼來帶他們,所以叫拋磚引玉。像法耀法師,耀禪法師,宗賢法師,都是比較早跟我學的;像聖富法師就晚一點,永光法師他們當時是沙彌晚一點,就是這麼一個過程。
努力去做,我就是是老老實實去做,沒想過要去設計出名什麼的。很多人說你怎麼不陞座,我說坐到哪裡去啊,我本來就不想當什麼方丈,不得已領著大家一起維護這麼一個地方,成就大家修學而已。所以說哪一天大家上了,我也不會覺得「啊!怎麼上了?」上了挺好,自己好好用自己的功。現在有人想學習也挺好,我會犧牲我自己一點時間來成全大家,將來大家如果能夠住持佛法,不是更好的事情嗎?所以我沒有別的想法。
很多人問我怎麼計劃的,怎麼設計的。我沒有任何設計。你看平興寺建的房子就像一個村莊,東一座西一座。它是不同時代連起來的,一般人剛開始不知道怎麼走。會走的,路路通哪,裡都通。這些房子都是互相連著的,這裡可以過去,後面也可以過去,那邊化城樓樓上裡面也可以通過去,到處都方便。最近連來三個風水先生,說醫療室那邊必須堵起來,不堵不行,這才堵起來。
平興寺建房子很隨意的,沒有看風水、沒有擇日子、沒有奠基、沒有落成、沒有開光,都是一路來。這裡的師父都知道,那個海雲樓,我們最多去灑個淨,別的事情就沒有做。有時候他們建議太多次了,就偶爾採納一下,我說一切都是人為的嘛。
我學佛的情況就是這樣,出家以後到這裡,慢慢地聽到佛學的一些道理;到了佛學院才接觸到了真正的佛學。十幾歲聽我媽給我講佛法,我媽從哪裡聽來的?是我姥姥告訴她的。她們講的都是一些民間流傳的小故事,我以為那就是佛法。後來真正學佛才知道,原來佛法是這樣,跟我以前知道的完全不同。所以要去學習,不學習人家講什麼你都分不出對錯。
與圓拙、法尊、正果、明真、巨讚等老法師的因緣
人的一生啊 ,因緣不可思議,你做過什麼,走過什麼路,親近過誰會改變你一生。我從佛學院畢業的時候,聽話,膽小老實,不敢說話,教務處覺得這個小孩不錯,就把我留在那兒打雜。打雜幹嘛呢,拖地板、夾報紙、收報紙、刻蠟板、油印。刻蠟板就是用鐵筆在蠟紙上寫字,油印有時搞黑糊糊的。這些事情,我會準時去做。
我有個同學提前畢業就去廣化寺學戒了,他一直寫信勸我去那裡。有一年放假我就過去看看適應不適應。八十年代廣化寺道風就非常的嚴謹。晚上到了休息時間就必須熄燈,誰沒熄燈被糾察看見,第二天就要點名的,即使圓老也不例外。有一次圓老熄燈晚了點,第二天就被糾察表堂了,就有這麼嚴格。有誰不去上殿也會被糾察點名。在廣化寺上殿,有一次我腿可能叉遠了一點,糾察一腳就踢過來了;你要是合不好掌他過去啪就打你一下子,沒有什麼商量的。「啪!你會不會合!」就這樣,很嚴 !剛去那裡我有點不適應,後來慢慢、慢慢習慣了就很喜歡那地方。
平時我們是自己學習,圓老告訴我們怎麼學,三大部一天看五頁,自己去琢磨。幾個學長,開始問幾次還可以,問多了他說你打擾人家了,後來不敢去問了,就自己弄唄。看不明白的地方來回看,實在看不明白就先放在那裡,就是這樣。妙老(妙湛法師)那時候在南普陀,接近的比較少。法尊法師從北京過來住在廣化寺小南山,我們住在一起有一年多時間,很好的因緣。他跟我們講過 《三主要道頌》。他老人家生活非常簡朴,全都是自理的,往生的時候也很好。有一天走路不小心磕了一下子,也沒怎麼樣,把他攙扶起來還好好的,送醫院去檢查,也沒有什麼毛病,過了兩天就往生了。這是我親近他們的一些事情。
在北京我親近過從四川來的正果老法師,他給我們講《俱舍論》,講《禪宗大意》。老法師講四川話,聽起來可費勁,幾乎聽不懂,等我能聽懂了他又不講了。還有一位湖南來的明真老法師,他給我們講過《百法明門論》,他說話完全是湖南鄉音,見面打招呼問吃飯沒,他就說「恰了沒」,開始也聽不懂,慢慢也適應了。我語言天賦還可以,當時外語老師還誇我英語發音比較標準,現在我到哪個地方學當地方言都學得比較快。到陝西就用陝西話跟他們聊天,到河南去也能跟那混,就這麼一個小技巧吧。
還有巨讚法師給我們講過開示,沒有真正講過課。我們有些法師是文革期間被逼還俗再來的,情況差不多就這樣。我接近的一些大德,現在這些大德們相繼都去世了,這是我跟他們的一些因緣吧。(來源:平興寺。此文根據界詮法師開示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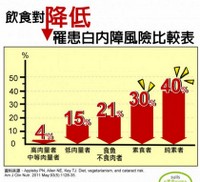












 夢參法師
夢參法師 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 印光大師
印光大師 玄奘大師
玄奘大師 大安法師
大安法師 如瑞法師
如瑞法師 慧律法師
慧律法師 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 省庵大師
省庵大師 界詮法師
界詮法師 善導大師
善導大師 妙蓮老和尚
妙蓮老和尚 聖嚴法師
聖嚴法師 蓮池大師
蓮池大師 其他法師
其他法師 憨山大師
憨山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