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言道「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人活一世難以一帆風順,常是苦多樂少。煩擾困於心,無以解決,常糾纏不去,積鬱成疾。故大德高僧那般泯除妄執、超脫生死的人生境界格外令人嚮往。因而,不少人通過和出家師父往來互動,親近佛法,感受僧家清淨坦然的生活之道。從古至今不乏名流大家交遊高僧大德的記述。
早在晉代,在家人同僧人的交往便見於書中記載。《晉書·謝安傳》載述謝安沒有出仕的時候,「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其中的同行者支遁,便是當時的東晉名僧,精通佛理,且有詩文傳世。
由於寺廟大都坐落於山林幽美的地方,與僧人一同登山涉水、吟詩談禪,是唐宋文人與僧人交遊比較多見的方式。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後,同東林寺僧人法演、智滿、士堅、神照等十七人曾遊覽廬山東林寺。白居易在《游東林寺序》中寫道:
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
山高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古時交通多有不便,住宿等商業模式並不發達。旅途之中,遇到可以寄宿的寺院,安頓疲勞的身體之餘,還能感受清淨幽美的方外境界,自是別具風情。翻檢文人集冊,可以發現大量「宿寺」的題詠。張繼《宿白馬寺》有云:
白馬馱經事已空,斷碑殘剎見遺蹤。
蕭蕭茅屋秋風起,一夜雨聲羈思濃。
古時寺廟接納掛單為羈旅人士提供方便。宋元之際的文學家鄧牧游雪竇山,「主僧少野有詩聲,具觴豆勞客,相與道錢塘故舊」,詩中的僧人熱情地邀他住宿;清人羅文俊游岳麓山,「山僧煮茗清談,燒筍侑脫粟,飽食一過,清芬可人」 ,領略到山中寺院的恬淡與素齋滋味。
由於寺廟多偏僻幽雅,僧人待客至誠,古代讀書人不少在寺廟臨時寓居,讀書備考。嘉祐元年(1056年),蘇軾到京城汴京參加進士考試,就寓居興國寺,在那裡與其弟蘇轍一道悉心準備,於次年二月通過禮部主持的進士考試,大獲歐陽修賞識,名震京師。
「客至莫嫌茶飯淡,僧家不比世情濃。」僧人對待來客都是平淡從容,不以貧富貴賤來區別。《南海寄歸內法傳》記載:過去佛陀住世時,客僧到來,他親自唱道:「歡迎!」印度僧人更是定下不少待客的禮儀,接待來客時,不論是新客、舊友、弟子或老朋友,都須上前說「莎揭哆」,即「歡迎!」如發現來的是新客,應接著說「窣莎揭哆」,即「非常歡迎」。來者幼小,請他在僻靜處居坐;來者尊老,則請他坐到堂前。
佛門講「待客以至誠為供養」,佛門的待客之道,其實就是平等至誠,不做什麼排場講究,而在平淡誠樸之間見真情。因為與人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持有一顆朴實、平等的心。
唐宋時期,不少士大夫佛學修養亦頗深厚,與僧人的交遊中留下了不少禪門機鋒公案。《五燈會元》中有這麼一則故事,蘇軾在荊南時,聽聞禪師玉泉皓機鋒敏捷,想領教一下,於是換了身便服去拜見。
玉泉皓問:「尊官高姓大名?」蘇軾故意說:「姓秤,就是秤天下長老的秤。」禪師突然大喝一聲道:「那你稱一稱我這一喝有多重?」蘇軾無言以對,對禪師以尊禮相待。
寺院是僧人們主持弘法之場所,自有其清淨莊嚴。善信們入得寺院,虔敬禮拜諸佛菩薩之餘,誦經品茗,漫步靜心,本足以調適心情、減輕憂慮。佛門有云:「世情看淡一分,則道念增長一分。」出家人求無上佛道,他們遠離俗念,清淨高潔,我們本不宜多有打擾。但若有機緣,於僧人中遇一善知識,得其引領,既可修習佛法,又可學其品行高潔,也是夙有佛緣的歡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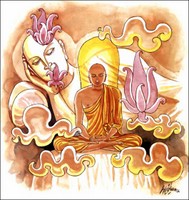






 慧律法師
慧律法師 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 省庵大師
省庵大師 界詮法師
界詮法師 善導大師
善導大師 妙蓮老和尚
妙蓮老和尚 聖嚴法師
聖嚴法師 蓮池大師
蓮池大師 其他法師
其他法師 憨山大師
憨山大師 廣欽老和尚
廣欽老和尚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虛雲老和尚
虛雲老和尚 淨慧法師
淨慧法師 圓瑛法師
圓瑛法師 來果老和尚
來果老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