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禪宗有一個雪峰禪師,他在福建的一個道場做方丈。福建是沿海地方,有一個內陸的比丘來參訪他。去見過方丈頂禮以後,雪峰禪師就問了,你從什麼地方來?這個禪師說,我從內陸很遠,從西北那個地方一路走到南方,來求見您老。雪峰禪師說,你一路辛苦了,走這麼遠的路。這個禪師說,仰慕道德,不憚辛勞。仰慕您高超的道德,所以我不害怕辛勞。
你來找我幹什麼呢?請和尚開示。雪峰禪師就說:出去。講兩個字而已,就走了。
出去,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我們凡夫的一念心,都是習慣在有相的境界分別活動,在色聲香味觸法的境界活動。你要我開示,我就告訴你一個方法好了,你不要在色聲香味觸法的境界活動了,從色聲香味觸法的境界裡面出去。出去到哪去呢?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呢?你進入到畢竟空的境界去,這就是出去,剛好是這句話,從假入空觀。
就是一個初學者不適合在假名假相的境界中分別,你應該要先淨化你的自性執,應該先做這個工作。所以雪峰禪師說,你先出去好了,你現在還不是在假名假相分別的時候,這個叫二諦觀。這個地方的二諦主要偏重在真諦,依止世俗諦而趨向於真諦,重點還是在真諦。亦名慧眼,慧眼就是空觀的智慧。亦名一切智,因為一切法的總相就是空,它能夠通達一切法的總相,所以叫一切智。
這個空觀,看智者大師的證果次第,把它安排第一個,它是大乘菩薩的一個基礎的觀法。這怎麼說呢?我們行菩薩道,發了菩提心,菩薩發阿耨多羅三邈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這個菩薩開始去弘揚佛法廣度眾生,做各式各樣的義工來實踐他的菩薩道,他有這樣的一個心情要利益眾生,但是這個菩薩的內心要如何地安住自己?
我們剛開始在安心是依止業果的道理,思惟我們的行為有善業、有罪業。罪業的因緣會使令我們墮入到卑賤痛苦的果報,善業的因緣會使令我們成就尊貴快樂的果報,我們剛開始是依止這樣的思惟。所以我自己的安心,應該安住在善業,要避免自己去造罪業。我在度眾生的時候,別人怎麼樣我不管,我要求我自己不造罪業,安住在善業的境界,深信業果,斷惡修善,剛開始菩薩是這樣,這是對的。
但是慢慢慢慢這個菩薩事業越做越大,所緣境越來越廣,遇到了人事因緣也就越來越複雜了,慢慢地他會覺得這樣的道理已經不足以安心了,因為很多很多的錯綜複雜的人事因緣,不是善惡這兩句話就能解決的。世間上的很多事情是不能講清楚的,這個時候他開始感到弟子心不安。雖然我要求我自己斷惡修善,但是發覺這樣的道理還不足以安心。
那麼這個時候菩薩應該怎麼辦呢?就要進步,從假入空。就是說你不要分別誰對、誰錯,他對你錯,這些有相的善惡業果完全放下,你安住在一切法畢竟空的空寂的體性上去。把你心中的所有的名言分別全部的停下來,你會發覺到:哎呀,這是一個大安樂處啊!在這個境界裡面都不必講任何的理由,也不必為誰辯解,你內心當中跟你的真如佛性念念地相應,那種寂靜的境界,這個就是最大的安樂處。
這個菩薩道的大悲心,他是依止空性發動出來的,不是依止我執、我見。這個就是從假入空觀,亦名二諦觀,亦名慧眼,亦名一切智。這是通達一切法的總相的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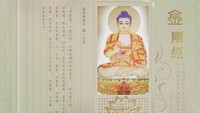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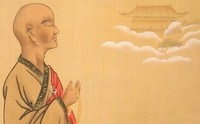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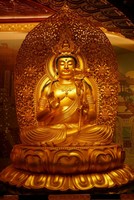

 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 來果老和尚
來果老和尚 道證法師
道證法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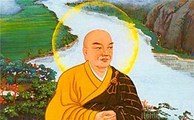 蕅益大師
蕅益大師 夢參法師
夢參法師 如瑞法師
如瑞法師 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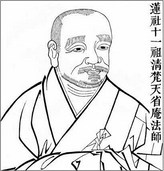 省庵大師
省庵大師 妙蓮老和尚
妙蓮老和尚 其他法師
其他法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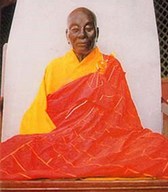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淨慧法師
淨慧法師 太虛大師
太虛大師 淨界法師
淨界法師 星雲法師
星雲法師 印光大師
印光大師